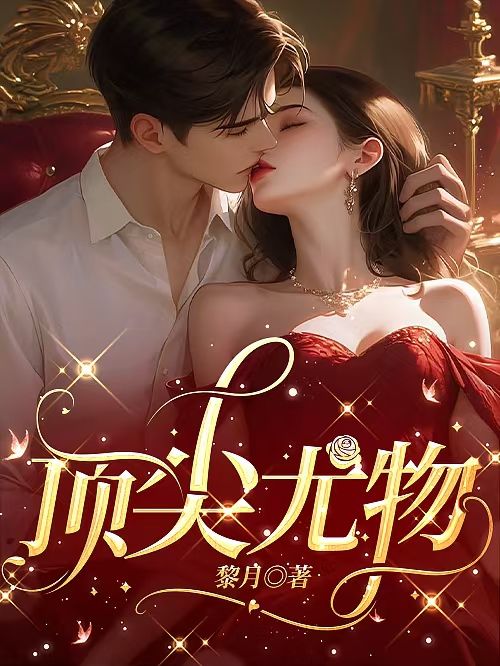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
第四章 我赤著足,在顧沉麵前,賣弄風騷
我轉身看見了黎靳。
黎靳年輕有為,是診所老板,也是Eric先生給我安排的心理醫生。
他有點忙,讓我在診室等他。
我拖著疲憊的身體,在狹小的診室睡著了。
入夜,我做了一個夢。
夢裏,我回到了十八歲那年。
那時,我還是宋家的掌上明珠,那一年我遇見了顧沉。
我瘋狂喜歡上了他,我寫給顧沉的情書足足裝了兩個大抽屜,我瘋狂地追了顧沉四年,終於在二十二歲那年,如願下嫁。
新婚夜,沒有我想象的美好。
顧沉將我困在婚床上,肆意折騰,那夜很疼很疼。
一個月後,爸爸中風癱瘓,而我被車撞成植物人。
顧沉仍不放過我,他恨我,在我身上繼續發泄。
那時我才知道,他對我,從未有過愛。
顧沉侵吞宋氏集團後,我這個妻子,便失去利用價值。
那夜烈火焚身,我的皮膚灼傷,我痛苦殘喘。
指尖握緊床柱,掐出血肉來,當白骨森森,那枚象征愛情的婚戒從我的指尖脫落,一聲清脆聲音,像極了我對顧沉愛的悲歌。
我在烈火中掙紮,隱約聽見,顧沉發瘋的聲音。
他說:“宋妍懷孕了。”
我吞沒在火苗裏,最後的意識是,顧沉模糊的麵孔,落下一滴眼淚。
我想,原來顧沉竟也會哭。
他不是恨我麼?
......
一陣夜風拂過,冰涼刺骨。
我從夢中醒來,一臉是淚,胸腔中仍殘存著恨意。
黎靳站在診室門口,靜靜注視我。
等我平靜下來,他才走進來,坐到辦公桌前抽出一本病曆:“最近怎麼樣?還會失眠嗎?”
我仍是失神,喃喃開口:“我遇見了顧沉,我成功引起了他的注意。”
我從破舊的背包裏,掏出那十萬塊錢,嘴唇顫抖:“他用宋家的錢買我一次,我被迫跪在他的跟前,但是我沒有讓他得逞。”
黎靳看著我,眼裏有一絲同情:“不怕......以後沒機會了?”
我何嘗不知道,顧沉的謹慎與挑剔,但我更清楚如果我從了,以後隻配跪著服侍顧沉,我在他麵前將沒有一絲尊嚴,這不是我要的。
我咽下苦澀道:“我可以等。”
黎靳沒再說什麼,給我填單子,開了主治失眠的藥物。
臨走的時候,我問黎靳:“Eric先生願意見我了嗎?”
Eric先生是救我的人,我想當麵謝他,但一直到現在,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。
黎靳意味深長,淡笑:“總會見到的。”
......
後來,很長一段時間,顧沉沒再來會所。
我不禁焦灼。
聖誕前夕,MINT會所舉辦一場狂歡派對,缺少一個芭蕾舞者。
我輾轉得知,顧沉會參加派對。
於是,我主動報名,要跟男舞伴在鋼琴上赤足跳舞。
一層層角逐後,我拿到了名額。代價是我要穿著撩人衣裙,在權貴男人麵前賣弄風騷,我要用我白嫩的腳尖,挑起他們感官的刺激。
平安夜那晚,MINT會所尊爵包廂。
我換上薄透的長裙,曲線畢露,眼角一尾朱砂痣化為勾人妖精。
我赤著雪足,踩在男舞伴的腳背上,當我抬起小腿時,那一截纖細的嫩腿微微顫著,勾動著在場所有男人的心臟,而後我細臂微展,像是一隻美麗脆弱的朱鹮。
顧沉的目光,一直落在我的身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