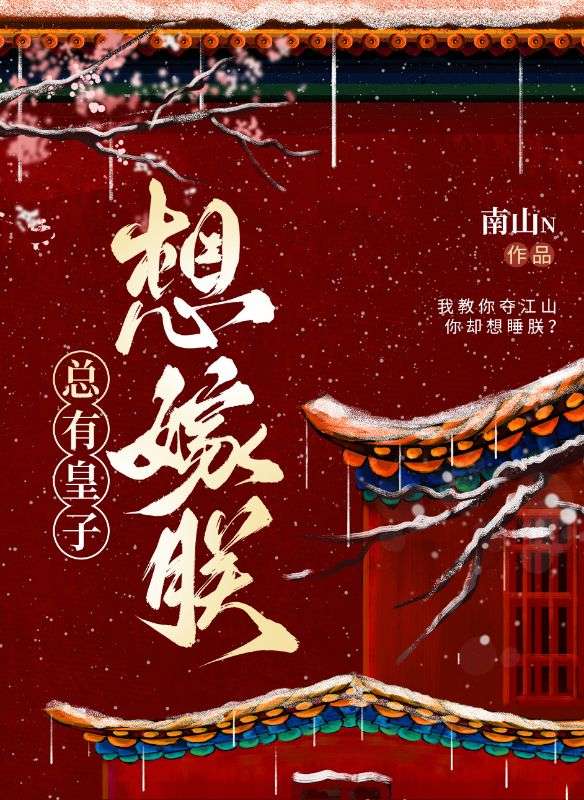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
第18章
救駕
將離心急火燎趕去流星閣。
衛家敢燒死皇帝,就更不會放過儲君,太子危矣!
垂雲大殿通往流星閣需要經過一條綠蘿小道,兩側橫七豎八躺著不少屍體,將離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,天殺的,太子要是死了,這帝師也做到頭了。
兩側灌木叢似有人頭晃動,將離蜻蜓點水一躍而起,揪住那腦袋上的頭發就往道上一甩,竟是將之瑤。
她摔得四仰八叉,見是將離,恨得咬牙切齒:“他們都死了,你怎麼沒死?”
“你都沒死,我怎麼好意思先死!”將離懶得理她,拔腿就走。
將之瑤撲過來拖住大腿,“太子哥哥被壞人綁了,都是你這個災星害的。你不許走!”
將離蹬腳,愣是沒蹬開她,怒火上頭,“你再拖著我,太子人頭落地,你這輩子休想當太子妃!”
將之瑤攥住她的袍角不撒手:“你帶上我。”
將離像提小雞一樣將她拎起來,“能不能走?不能走別礙事。”
將之瑤對太子的確上心,一瘸一拐走在前邊帶路:“能,我要救太子哥哥。”
這種時候怎麼好讓將離一個人出風頭,她必須在。
將離眉頭緊蹙:“幾個人?”
“兩個。”將之瑤舉著雙手,默默比了個剪刀,改了口。
將離嗤了嗤,不足為懼。
流星閣鴉寂無聲,東宮伺候的太監婢女屍首橫七豎八地倒在血泊之中,大殿門口由兩個黑衣人把守。
將離小心翼翼靠近,寒光一閃,兩道身影悄無聲息地倒下,她低聲對身後的將之瑤叮囑道:“待外頭別動,我去把太子帶出來!”
她一踹門,殿內燈火通明,烏泱泱的人頭看向她。
至少十七八個人,將之瑤這坑貨!
領頭的正持劍逼太子寫著什麼文書,東宮長隨天祿渾身血淋淋跪在地上,兩個黑衣人押著他的雙手,一人正高舉大刀要砍他的腦袋。
將離想也不想擲劍而去,正中那手舉大刀的黑衣人胸口,她一個鷂子翻身衝了過去,在黑衣人倒下之前拔出了劍,反手一揮,斬斷另一個黑衣人的脖頸。
天祿沒了束縛,低頭拾劍,與圍擁而來的黑衣人展開廝殺。
太子身側領頭的黑衣人一看架勢不對,索性也不要什麼文書,直接揮刀想殺死太子了事,說時遲那時快,寒刀隻差須臾就要砍斷太子脖頸,將離挑劍一抵,刀刃相接迸裂火星;太子脖頸一寒,發絲斷了幾截,飄飄灑灑、失魂落魄,骨頭酥軟,重重跌落在地上。
隻差一點,隻差一點呐!
他摸著自己的脖子,看著將離與四五個黑衣人廝殺在一起,惶恐驚懼地向後退坐了好幾步:“阿離,小心!”
有黑衣人朝太子砍去,將離飛身而上,撲了過去,護住了太子,自己卻被砍中了手臂。“殿下,你快走!”
“天祿!帶太子先走!”將離大喝。
天祿殺紅了眼,“是!”
太子躲在天祿身後,步步往門外退,“阿離,你小心呐!!”
將之瑤不知何時偷偷摸到門口:“殿下,快跑!”
天祿護著太子退出大殿,將之瑤眼珠子一轉,撕開衣角將大殿門用布條捆得死死的。
裏麵的黑衣人無論如何撞,都打不開門。
“好啊!都是你壞了我們的好事!”
他們將怒火全部指向了將離。
將離啐了口唾沫,沒有廢話揮劍而上。
這些人都是高手,招招淩厲,出手就是絕殺且人數眾多,如車輪反複進攻,將離力有不逮,手臂被劃破了好幾道血口子。
他娘的,將離怒罵了聲,扯破衣角當布條將手與刀綁死,再度陷入血戰。
李承昊循著蹤跡追來流星閣,踢開大殿的門,看到的是極其慘烈的一幕。
將離握劍單膝跪地,滿是豁口的劍筆直插在地上成了她的支柱,瘦削的身姿搖搖欲墜,一襲白袍血染成梅,滿臉都是未幹的血跡。
長睫微微一抖,兩滴血如淚滑落,她的唇輕顫,卻發不出聲音。
黑衣殺手的屍體如天女散花般倒在地上,血流成河;已分不清哪些是黑衣人的血,哪些是將離的血。
她就像是從血之湖泊中傲然而生的白蓮,妖冶又空靈。
天地皆濁,唯她獨清。
“他娘的!”李承昊像是被重物撞擊,心如佛鐘回蕩嗡嗡,腦海一片空白。
他驚慌地衝過來,又氣又恨,“為了個太子,你不要命了!”
“我,強得可怕。”將離籲了口氣,手指蜷成拳死死握著劍,鬆都鬆不開。
李承昊解開她手上的布條,將她的手指一個一個掰開,劍咣當落在地上,手已經僵硬蜷曲。
他把將離的手放在手心來回揉搓,仔仔細細為她鬆弛筋骨,可她身上的傷太多了,手臂、背部、腿部,刀口雖淺,但滲出的血染紅了衣裳,小臉蒼白如紙。
李承昊一把打橫抱起她往外走,邊走邊呲:“是是是,你最強。天下第一強,行了吧,侍郎大人。沒死算你走運,這幫人可都是衛家重金豢養的死士。”
他的懷抱很燙,靠著很安定,將離浮唇輕輕一笑,沒有力氣接話;她似乎走了很長很長的路,已經精疲力盡了。
李承昊將他抱回大殿空地,雙慶在人群中翹首以盼,見到她滿身是血呆了呆,立刻迎上去。
“照顧好你家公子!”李承昊斜睨了一眼,確定雙慶攙扶好她之後才轉頭離開。
他身為禁軍總督,還有很多事要善後。
雙慶一步步攙著她回房:“您這是怎麼了?怎麼傷成這樣?”
“將之瑤在哪?”將離問,瞧見非掐死她不可。
“二小姐在前頭偏殿陪著太子,今夜好險,聽說宮變了。”
將離渾身像散了架,“去倒水來,我洗洗。”
雙慶哎了身退了下去。
將離就直接癱倒在地上,從袖中摸出那封信。
信口封著蠟泥還印著太傅將正言的私章,並未被拆封過。
將離展開信,熟悉而遒勁的字體迎麵而來,是將正言寫給北冥王李長白的。
北冥王親啟,
葉州至涼州大營約二百裏,吾與使團寅時出發,巳時三刻可抵達。
州與州之間山路多崎,天熱,團中有人難耐暑氣,怏怏未愈;
私以為,使團抵涼後暫歇二日再啟程去錫國為宜。
煉火熬油慢驅慢行,若有叨擾之處,望望王爺見諒。
鐵騎無需過早至鳴沙山坳口,以免徒曬勞累。
……
將離噌地坐了起來,屏住了呼吸。
葉州私煉鐵!
將正言用的是藏頭詩的寫法。
他想偷偷告訴北冥王,這麼說,葉州刺史屠光要反?
父親的死,難道是葉州刺史幹的?!
可惡,此人事發後痛哭流涕如喪考妣,她和朝廷都被屠光騙過了!
她迅速看下去:
另有寥寥數語乃思親之故附於信後,望王爺轉達吾兒。
父遙望明月昭昭,思蒼生疾苦輾轉難眠;
登州大旱顆粒無收,民易子而食;巴州山洪大澇,房屋瓦舍皆隨濁流覆滅,死傷無數;民無寸瓦、衣不蔽體、食不果腹,天災乎?人災乎?
西山有神龜,北嶽出螭虎,山崩地陷,異象頻出;星墜木鳴、國人皆恐。節度擁兵自立,百姓如浪而逐,國有分崩離析之勢。嗟呼!
世道亂而仁義崩,政出其令而無人尊,吾為帝師上愧天子,下愧黎民。楛耕傷稼、政險失民;為帝之師,需知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,非一人之天下。
吾兒入仕當心懷悲憫、肩挑蒼生,居廟堂之高不忘民之根本,輔天子施仁政以慰百姓疾苦;君不仁臣不敬則民不聊生,帝師當滌其心、濯其足,時時勸誡、警醒,心常懷憂。千人諾諾,不如一士諤諤。
惟望吾兒肩挑日月,篳路藍縷、以啟山林。
非千萬人吾往矣!
昭昭雲端月,此意寄昭昭。
……
明月昭昭。
這封信重複了幾次昭昭……
像是將正言特地寫給她的?
將離讀完已是淚流滿麵。
隻是,父親怎會猜到,有朝一日她會入朝議政做帝師呢?
一個謎團解開,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的謎團。
這場宮變來得遽然,卻又並非毫無征兆。
皇城司使謝世忠以戴罪之身迅速查清了整個案情。
貴妃為了二皇子聯合衛家密謀在避暑山莊對皇帝動手,事發前她端了一碗放蒙汗藥的參湯,迷暈了皇帝。
衛子廊作為內應,假借負責安防之便,悄悄放死士入島;他們本想借著月黑風高夜快速占領芙蓉山莊,誅殺太子,逼皇帝改立二皇子為儲君,可沒想到垂雲大殿竟燒起來了。
火燒大殿的又是另一幫人。
北冥戰事不斷,各項軍需資費陡增,地方災亂頻生,處處都在要錢;可國庫這些年早被占據六部要職的雀都世家一點點掏空了,根本沒什麼錢。
窟窿越來越大,賬目填不平,就無法應對皇帝問詢。
工部文戶部一合計,不妨就燒了垂雲殿,再以修繕為名虛增費用,糊塗賬糊塗辦,事後大家都能安枕無憂了。
縱火時,誰都不知道皇帝在大殿裏麵。
放火這件事吃力不討好,就交給寒門出身的湯憲來辦。
火是他放的,這鍋也當然得由他來背。
湯憲百口莫辯:“陛下,老臣冤枉啊!老臣忠心耿耿,這件事是文大人他們……”
工部尚書文若承直接打斷他的話,“陛下,湯憲竟敢火燒大殿,這是弑君啊!他目無君父、貪腐作亂,理當五馬分屍!”
堂下有利益牽連的大臣紛紛附議。
皇帝心裏頭明鏡兒似的,戶部的窟窿不是一日兩日了,這幫人是拿著湯憲的命來平賬呢。但火是他放的,的確該死。
湯憲這把刀,最終捅向了自己。
皇帝當場誅殺湯憲;文若承、顏直等因督辦不利連降三級;而將不棄有救駕之功,不但未被牽連,反而當場擢升為戶部尚書。
李承昊鬆了一口氣。
沒想到工部的人玩這麼大。
他們本來隻想弄塌個亭台樓閣讓湯憲貪腐工程款的事曝一曝,沒想到他自己把自己點炸了。
不得不說,臥龍鳳雛,得之可斷腿。
沒錯,皇帝的腿斷了。
貴妃被廢賜鴆酒;衛子廊淩遲;衛氏夷三族;
二皇子跪在殿中痛哭流涕,直說謀反案與自己無關。但這一次的眼淚再也打動不了皇帝了,他召了人抬進一個木箱,當著滿朝文武的麵:
“把這逆子關入木箱不得喂食喂水!”
“父皇,父皇!兒臣冤枉啊!父皇!”
二皇子被塞入狹小的木箱,身子隻能蜷縮著,不停在箱子內叩著木板。
太後在珠簾後幽幽一顫,哼,這算是殺雞儆猴嗎。
衛氏真是不中用,搭了台子讓他們唱戲也唱不成,廢物。
“皇帝,虎毒尚不食子,賜他一杯毒酒便是,何苦如此?”
皇帝斷了腿後他性情大變,像是知道自己時日無多,全然不想做麵上功夫,眼神陰鷙而狠厲:“朕往日的心慈,皆成了人盡可欺的怯懦。朕還沒死,有覬覦江山者,當如此子!”
滿朝文武皆跪地,蕭相高冷,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;有幾個德高望重的老臣實在不忍,出列求情,其中就有國子監祭酒崔永真。
“陛下,君仁,莫不仁;君義,莫不義;君正,莫不正。一正君而國定,君不鄉道,不致於仁,隻會徒增百姓恐懼,與夏桀何異!”
皇帝大怒:“放肆!崔卿之見,難不成子弑父,還是父之過了?你真是迂腐過了頭,枉讀聖賢書!”
“子弑父天地不容,可您如此殘暴對待兒子,定會被世人詬病!臣叩請陛下將此子交由三司,依大慶律法嚴懲!”
老臣叩首:“陛下!三思啊!”
“好好好!你們都和朕作對!你們忠的到底是他,還是朕?!”皇帝失去了理智,“那就都跪在此處,看著這個逆子斷氣!沒有朕的允許,不得起身!”
皇帝拂袖而去,滿朝文武戰戰兢兢。
幾個老臣就這樣對著木箱跪著,聽著二皇子在箱子裏發出的哀鳴,麵露惻隱和不忍。
太子躬身來到崔永真身旁,心有餘悸:“崔大人,您少說兩句吧。”
“太子殿下,二皇子乃你手足之情,縱然他該死,也不該如此受折磨,此非人倫亦非國法,而是暴政、惡行。請太子殿下去求陛下收回成命吧!”
太子驚懼地向後退:“崔大人,你這不是為難孤麼。”
崔永真欲再說些什麼,可最終還是失望地閉上了眼睛。
將離對著他挺直的脊梁躬身行禮,“崔大人切勿動怒,晚輩去勸。”
李承昊輕輕扯動她的袖袍,示意她出大殿。
“陛下正在氣頭上,緩緩再諫。”
將離頷首,抬眸恰巧與他目光相交,兩人不約而同又錯開視線,都有些不自在。
自芙蓉山莊回到雀都後,兩人這是頭一次得空私聊。
李承昊護駕有功,陛下將讓他從原先的禁軍都指揮使兼管殿前司都指揮使,忙得飛起。
將正言書信中所述的葉州私煉鐵之事幹係甚大,兩人商量後決定暫時不向朝廷舉發,私下飛鴿傳書北冥核實。
師爺孟賀嶂已啟程進京了,此刻急也無用,隻能等見到人再細問了。
“你……還好吧?”將離想起那日在火中,他多次被掉落的木頭砸到,事後也沒來得及問他傷勢。
而比起身體的傷,更折磨人的,還有流言。
雀都不知從何處傳出風聲,廢妃衛氏和二皇子鋌而走險謀逆,是因為李承昊的身世。
傳言李承昊是陛下與已故北冥王妃的私生子,陛下甚至有意立他為儲君。
流言四起,如投石落湖,很快就擴散出去,酒樓瓦肆說書的唾沫子橫飛,像是各個都親圍在床頭見證過這段不堪的情事。
大街小巷的話本子都出了好幾個版本了。
李承昊斂眸默不作聲,他大體知道將離想要問的是什麼,可他並不在乎。
他在乎的是另一件事,“你小時候可曾……”
救過一個孩子,給過他銅錢和棉衣?
他還沒來得及問,東宮的人就來請將離去議事了。
將離拱手道別,李承昊隻能把疑問又咽回肚子。
往宮外走時,他又不自覺回頭看將離的背影,疑惑在心頭越滾越大,像是巨石,壓得他喘不過氣來。
“玄暉,你說,昭昭有沒有可能是個男的?”
他有些難以啟齒,可此刻他很希望是如此。
畢竟四五歲的孩子,男女都長得挺圓乎。
“那……不能吧?”玄暉似乎看穿了什麼,“爺,屬下覺得,昭昭是男是女不重要,重要的是,將侍郎……哦不,是將尚書是男的。您是不是對他有意思?”
李承昊像是聽到天方夜譚似的,捧腹大笑,直笑彎了腰,手指著玄暉:
“你在說什麼胡話呢!簡直笑死人了!我,李承昊,我會喜歡他?天下那麼多美女我找誰不行,非要挑個男人!滾一邊兒去,再讓我聽到這話,打爆你的狗頭。”
他罵完怒氣衝衝管自己走了,獨留玄暉一人在風中淩亂。
“我不過是隨口一問罷了,那麼大反應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