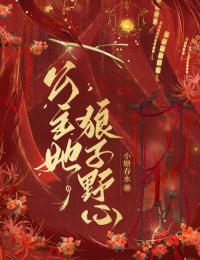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
第10章
元日過後,又下了幾場大雪。甘露殿內,上好的銀霜炭在鎏金狻猊爐裏無聲燃燒,蕭玥跪坐於禦案下首鋪著的厚實茵褥上,纖白如玉的手指在堆積如山的奏疏間翻飛,將來自三省六部、禦史台、地方州郡的文書分門別類,條理清晰。
前些日子崔家舉薦的兩位大儒,弘德帝準了其二人入弘文館,專責教導諸位皇子經史。
張公望,前朝文宗,門生遍天下,一部《春秋正義注疏》為天下士子圭臬;李伯淵,清流領袖,辭賦冠絕當代,歸隱前曾任國子監祭酒。這兩人,皆是文壇執牛耳者,皓首窮經,名動天下,卻無半點實權在握。
崔氏此舉,甚是高明。蕭玥心中冷笑。張、李二人如兩座活生生的文峰矗立在弘文館,不費崔氏一兵一卒,便將天下寒門士子的仰望之心盡收囊中。清流之望,無形無質,卻重若千鈞,這才是真正的四兩撥千斤,比染指兵權更令帝王忌憚,也更難揪出錯處。
指尖劃過一本奏疏,蕭玥動作一頓。她將其抽出,置於整理好的一摞奏疏最上方,神色如常地呈到禦前。
弘德帝正批閱軍報,隨手拿起,目光掃過,正是禦史大夫韋遠的筆跡。奏疏彈劾崔氏“私結清流,以虛名邀聖眷,其心難測”,更直指崔家近來“門庭若市,車馬喧囂,有逾矩之嫌”。
韋遠那雙老辣的眼睛,從不揉沙子。崔氏接連舉薦大儒,聲勢浩大,看似為皇子師,實則是在向天下士林招手,編織一張以文華和師道為經緯的大網。
弘德帝的指尖在奏疏上“逾矩”二字處重重一叩,紫檀木案發出沉悶的聲響。他忽然嗤笑一聲,那笑聲裏聽不出多少暖意:“韋遠這老匹夫,這些時日是恨不能把崔家的門楣鑿出洞來。”?
“禦史聞風奏事,糾劾不法,本就是他們的職責所在。”蕭玥的聲音溫潤如玉,不疾不徐,“韋大夫忠心體國,得此賢臣,是父皇之幸。”
蕭玥起身提起一旁溫在紅泥小爐上的鎏金銀壺,將溫熱的泉水注入弘德帝麵前那隻瑩潤如玉的天青釉茶盞中。碧綠的茶湯打著旋兒注入,嫩葉舒展沉浮,嫋嫋熱氣蒸騰而起。蕭玥話鋒悄然一轉,帶著少女天真的疑惑:“隻是兒臣前日翻閱書籍,偶然看到張公望先生所注的《春秋》,開篇便大談‘尊王攘夷’,字字鏗鏘,令人心折。卻不知他今日入得弘文館,為皇子們開講時,是著重講那周天子垂拱而治的威儀呢,還是…更推崇齊桓公九合諸侯、一匡天下的霸業之道?”
殿內陡然一靜,狻猊爐裏的銀霜炭“劈啪”爆出一點火星。
弘德帝端著茶盞的手停在半空,銳利的目光瞬間釘在女兒臉上。那看似天真的疑問,卻像一把淬了冰的匕首,精準地挑開了崔氏此舉最核心的隱患——尊的是哪個“王”?攘的又是哪個“夷”?以清流大儒之口教導皇子,灌輸的究竟是忠君守禮,還是潛藏了能動搖國本的“權臣輔政”之理?蕭玥以《春秋》為引,借古喻今,將韋遠直白的彈劾,點化成了更致命,也更誅心的詰問。
茶湯的熱氣在帝王冷峻的眉眼間盤旋。良久,弘德帝緩緩啜了一口茶,將茶盞輕輕放回案上。他並未直接回答蕭玥的問題,目光卻重新落回韋遠的奏疏,指尖在“門庭若市,車馬喧囂”一行字上緩緩摩挲,仿佛在掂量著這八個字背後的分量。
“門庭若市…”弘德帝低語重複,語氣辨不出喜怒。
他又想起了先前崔貴妃請旨為許充容晉位一事。他當時當場點破了許充容與隴右節度使的舅甥關係,斥責其“伶俐”,罰抄《女則》以儆效尤。如今想來,那試探豈止是“伶俐”?韋遠奏疏中“車馬喧囂”的崔府門庭裏,是否就有著來自隴右,甚至其他邊鎮軍鎮的說客?
後宮安插親信,朝堂籠絡文臣,邊鎮勾連軍將。崔氏想要的,哪裏隻是一個後位?他們想要的,是內外勾連、文武相濟,將三皇子蕭瓏拱上儲位,乃至最終掌控這大梁江山!一股殺意瞬間從腳底竄起,直衝頂門。
可眼下還動不得崔氏......弘德帝按下心頭的怒火,目光掃向侍立在一旁、幾乎屏住呼吸的李福安,冷聲吩咐:“你去弘文館告訴褚良,張、李二位先生初入弘文館教學,朕恐學生們欺生,讓他多看顧著些。尤其是二位先生所授經義,務必確保原原本本,字句清晰,莫要讓年少之人聽岔了,解歪了。明白嗎?”
“奴婢遵旨。”李福安聲音有些顫抖,當時怎麼就鬼迷了心竅,以為貴妃會是繼後的不二之選,竟還想著做個順水人情,如今看來,陛下分明忌憚崔氏甚深。
退出殿門時,他感到背心一片刺骨的冰涼,竟已被冷汗浸透
殿內重新陷入死寂,隻剩下炭火細微的劈啪聲。蕭玥垂眸靜立,姿態恭謹柔順,低眉斂目,仿佛剛才那幾句攪動起驚濤駭浪的話語,真的隻是她一時天真的好奇,與她本人毫無幹係。弘德帝的目光掠過女兒沉靜的側臉,那份沉靜讓他心中的疑慮並未完全消散。無論她本意如何,今日這一問,已如投入深潭的石子,必然在朝堂和後宮激起針對三郎的暗湧。最終,帝王的目光投向窗外......風雪中的宮闕,皇子們的明爭暗鬥,亦如這漫天雪霰,無聲無息,卻無處不在。
他忽然有些乏累,這滔天的權勢…當真是世間至毒之物!翻弄乾坤,顛倒倫常。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…何其荒謬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