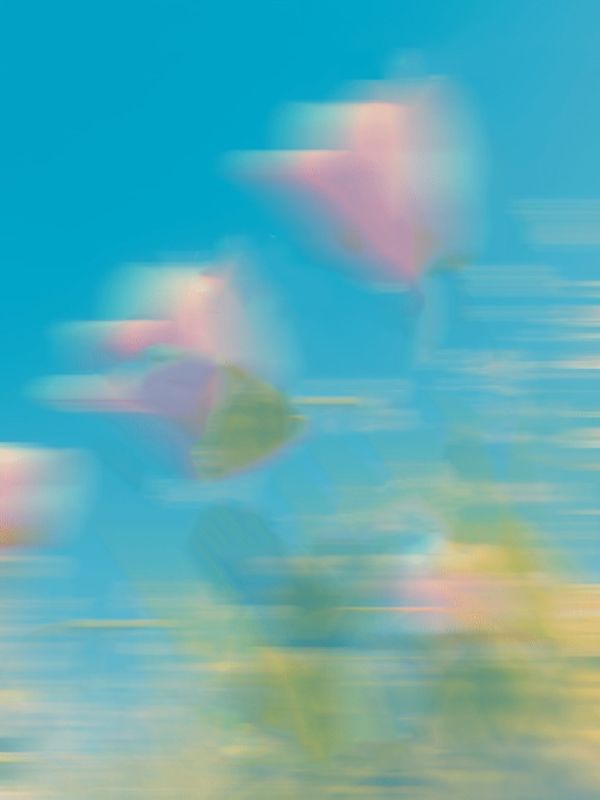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
第二章
我起身攔住他:“陸總,這是我的辦公室,不歡迎你,請你離開。”
陸硯修不滿我的態度,眉頭不悅地蹙起:
“池清荷,你在和我鬧脾氣嗎?”
我別開視線。
他卻不依不饒地逼近,幾乎將我困在他與牆壁之間,審視的目光在我臉上流連,語氣篤定:
“你吃醋了。”
“沒有!”
我幾乎是立刻反駁,聲音帶著不易察覺的顫抖:
“你和蘇婉在一起,我真心為你高興。”
陸硯修嗤笑一聲,仿佛聽到了天大的笑話:
“池清荷,別裝了。我們認識多少年了?你喜歡我多久,以為我不知道?”
他眼底帶著幾分戲謔,慢條斯理地撕開過往的傷口:
“記得嗎?就因為我隨口說想要一萬顆星星,你就傻乎乎地沒日沒夜地疊,手指酸痛連筷子都拿不住。”
“我半夜三點想要吃蛋糕,你不顧風雪親自去買,淋得渾身透濕,出現在我家門口......”
“還有大三那年,我們去墨爾本度假,下大雪,我們一起出了車禍,你把受傷的我抱在懷裏,說如果我有事,你也不活了......”
他一樁樁,一件件,如數家珍般將我那些卑微的付出攤開在陽光下。
心口傳來細密而尖銳的疼痛。
原來他一直都知道,知道我漫長而無聲的暗戀,知道我所有小心翼翼的討好。
在蘇婉出現之前,陸硯修待我,並非如此冰冷。
至少,在那場大雪時,他滿頭鮮血的躺在我懷裏,也曾有過真切的情義。
可如今,這些回憶都變成了玻璃渣裏的糖。
甜意猶在,卻紮得我血肉模糊。
見我臉色愈發蒼白,陸硯修像是找到了打擊我的利器,愈發得意:
“讓我再想想,你還為我......”
我攥緊的拳指尖泛白:
“說夠了嗎?說夠了就請你出去。”
陸硯修當然不可能就此罷休。
他走到我的辦公桌前,熟練地拉開最下麵的一層抽屜,拿出了一個相框。
我心下一沉。
一個相框被他拿了出來。
那是大學時我和他唯一的合照。
照片上的我們,笑容青澀而真摯,曾被我視若珍寶。
他慢條斯理把照片從相框中取出來,扔進了碎紙機。
池清荷,我認識你二十多年,一直把你當妹妹。”
“可你呢?從小就懷著這種齷齪的心思!我早就告訴過你,我心裏隻有婉婉,你怎麼還能如此恬不知恥地貼上來?”
說完好像還不解氣,又附在我耳旁:
“對了,還要多謝你那晚的‘成全’。如果那天晚上是你......我一定會殺了你。因為,你、不、配。”
我垂下頭,沉默地承受著這一切。
指甲深深陷入掌心,帶來一絲維持清醒的痛感。
他顯然將我的沉默當成了無地自容,嘴角揚起勝利者的弧度:
“池清荷,別把事情弄得太難看。今晚七點,準時到場。”
我用沉默,當成最後的抵抗。
他卻扯唇一笑,神色間滿是惡劣:
“我記得,你舅舅手上那個項目,似乎還壓在我這裏審批?”
“清荷,你說,這個項目,是批,還是不批呢?”
那個項目,舅舅投入了無數心血,跟進了大半年。
我不能讓他的努力因我付諸東流。
胸腔裏堵著難以言喻的澀痛,我深吸一口氣,逼退眼眶的濕熱,終是向現實低頭:
“我會準時到。”
陸硯修得到了想要的答案,果然說到做到。
他當場拿出手機,撥通了電話,雲淡風輕地批準了那個項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