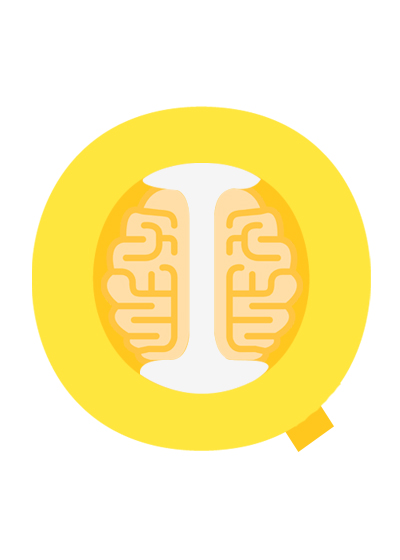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
第一章
婚禮前三天,陪老婆最後一次試婚紗的時候,電話突然響起。
“小宇。”
僅僅兩個字,我便猜到了是誰。
但我們已經八年沒有聯係了。
上一次見麵,還是那個男人陪她產檢。
“有事?”
聽到我的回答,電話那頭的呼吸驟然變重,聲音也有些急切:
“小宇,聽說你要結婚了,能不能讓我見見你爸?”
“我們一家三口團聚。”
團聚?
我低頭,摸上胸前藏著黑白遺像的項鏈,輕笑一聲。
“想見我爸?等你死了再說吧。”
1
掛斷電話,老婆正好從試衣間出來。
看到我胸前打開的項鏈,她笑容肉眼可見地淡了幾分。
“又想爸了?”
她溫柔地靠近我懷裏,帶著點小心翼翼地試探。
“都過去這麼多年了,我們結婚真不邀請你媽嗎?”
我摟著她的手一僵,冷冰冰的。
“她八年前就不是我媽了。”
“可是......”
老婆還想說什麼,我的電話卻先一步響起來。
是爺爺。
他說我媽賀晴不知道從哪兒得知了我要結婚的消息,纏著他非要來參加我的婚禮。
還問我,要不要把我爸去世的消息告訴她。
我冷著臉,一字一字回複。
“不用理她。”
自從八年前的那件事起,我就再也沒有媽媽了。
爺爺歎息了一聲,沒有勸我,隻是快要掛電話的時候,突然說了一句:
“小宇,其實當年的事,你媽也不容易。”
爺爺竟然原諒她了。
我眼眶一紅,差點笑出聲。
我不明白。
明明當年被欺負、被趕出家門、被活生生氣死的人是我爸。
八年過去,為什麼說她不容易?
難道就因為她是我媽?
和我有那麼點所謂的血脈相連?
別招笑了。
掛斷電話,我換下了身上的西裝,拿鑰匙出門。
老婆擔心地追出來:
“瀚宇,你去哪兒?不回酒店了嗎?”
“不回去了,去公墓,看看我爸。”
黑色奧迪在南山公墓停下。
我下車,熟練地買了瓶白酒,在第三排第七個墓碑前跪下。
“爸,我來看你了。”
我將酒瓶旋開,熟練地倒在地上,又扯過清理雜草的老婆。
“這是你兒媳婦,林妍,我們後天就要結婚了。”
“還有,她來找我了。”
我頓了頓,壓下哽咽:
“爺爺說,她想來參加我的婚禮,我拒絕了。”
“你放心,我永遠不會替你原諒她。”
“爸,我想你了。”
我一邊說,一邊用手小心地擦去墓碑上的灰塵。
露出一張和我有五分相似,溫柔帶笑的麵孔。
那是他最開心的一天。
妻子的公司上市,兒子考上了重點大學。
升學宴上,他看著我和我媽時那副毫不掩飾地愛護和驕傲,被攝影師定格。
成了他這些年來,最幸福的畫麵。
那時的我們永遠不會想到,這張照片,在八年後。
也刻在了他的墓碑上。
2
回去的路上,我靠著車窗,任風吹幹眼角的濕意。
老婆為了安撫我,絞盡腦汁地講笑話逗我開心。
我鬆了嘴角,剛要說話。
忽然,眼尖地注意到了酒店門口徘徊的女人。
“你來幹什麼!”
我整個人都豎起了尖刺,猛地衝下車,質問她。
賀晴看見我,臉上原本帶著的笑意,也頃刻間變成了無措。
“我......我就是想來看看你。”
“我是你媽,你結婚,我當然要......”
“你不是我媽!”
我打斷她,頭也不回地拉著老婆往酒店裏走。
“你要是還有點良心,就別再讓我見到你。”
門廳的反光裏,我看見賀晴追了兩步,聲音被風撕扯著飄進來:
“小宇!你至少告訴我......你爸他還好嗎?”
我腳步一頓,又迅速抬起。
還好嗎?
人都死了,當然好了。
走到前台,我剛準備通知酒店不許賀晴進來。
經理卻主動找到我:
“抱歉沈先生,您的婚禮場地,被人訂走了。”
“什麼?”
我愣了一下,接著立刻反應過來。
“是她幹的吧?”
我沒有指名道姓,經理卻麵上一虛。
“我們不能透露客人名字,不過她說隻要能跟您和您的父親見一麵,場地就無償讓給你們。”
老婆擔憂地看著我:
“瀚宇,要不算了吧......”
“我再去聯係別的酒店。”
我搖了搖頭。
“沒用的。”
“隻要她認定的事情,再怎麼折騰......都沒用。”
這個道理,八年前我就懂了。
掏出手機,我遲疑了很久,還是撥通了那個號碼。
“明天上午十點,咖啡廳,我們見一麵。”
我聲音冷得出奇,電話那頭的賀晴卻如獲至寶。
“誒,誒!小宇,我一定不會遲到,你爸他是不是還喜歡......”
沒等她說完,我直接掛了電話。
晚上,二叔的飛機也到了。
八年前,他還在海外留學,什麼都是後來才知道。
八年後,見到我的第一麵,他就紅了眼睛。
“那個該死的畜生怎麼還有臉來找你的?”
他握著我的手,整個人都在顫抖。
“八年前,是她親口說的不認你這個兒子,現在怎麼敢有臉回來參加你的婚禮?”
“她配嗎?”
“還有你爸......”
二叔哽咽了一聲。
“他怎麼就那麼賤,寧願自己打工也要省吃儉用地供那個白眼狼讀書。”
“後來好了,她功成名就了,做的第一件事卻是出軌找小三,把你爸活生生氣死。”
“你爸死那年,才四十五歲啊。”
二叔泣不成聲,我閉著嘴巴,沒吭聲。
因為他說得對,我爸就是太賤了。
他跟我媽結婚的時候,我媽還隻是一個窮到連飯都吃不上的精神小妹。
母親早死,父親是個賭鬼,人生一塌糊塗。
可我爸就是傻,因為上學路上被她救了一次,於是整個心都丟給了她。
十八歲,我爸為了她放棄學業,打工供她上學。
二十二歲,他們結婚,生下了第一個孩子,也就是我。
四十五歲,我考上大學,我媽出軌。
罵他罵的最狠的一句話就是:
“我不要臉,但你十八歲就為了我進廠打工,本科學曆都沒有,你有什麼臉?”
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我爸露出絕望的眼神。
那眼神太痛,八年過去了,我還會在夢中驚醒,後悔自己不該。
不該把我媽出軌的消息,告訴了他。
3
第一次發現我媽出軌,是在我的升學宴。
那是我爸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。
我媽的公司上市了,我也考上了重點大學。
整個宴會,他臉上的笑容就沒停過。
直到我借著透氣的理由,躲到了陽台和同學發消息。
幾步外,我媽跟一個男人抱在了一起。
那男人我認識,是我爸交往了十八年的好兄弟。
我人生中第一雙球鞋,就是他送的。
我愣在了原地,腦子一片空白。
等到再恢複意識,已經尖叫出了聲。
那聲音太尖、太過撕裂,甚至帶了血。
我爸擔心地跑過來,見到這一幕,形神俱裂。
我聽見他問我媽:
“為什麼?”
“為什麼是他?”
那個被他當成兄弟,處了十八年的好朋友。
“為什麼要在今天?”
在他兒子升學宴的日子。
之後的事情我記不清了。
我隻記得,那晚我們家的燈徹夜未眠。
媽媽拿著手機發消息,提示音一條接著一條。
我爸呆坐在一邊,臉上的神情凝固。
他們達成了協議:我媽和那個男人斷了,我爸假裝事情沒發生過,別影響我上學。
那時我爸還天真的以為,可以重新來過。
直到第二次,我爸買菜回家。
臥室的門開著,兩個人衣衫不整的摟在一起。
而邊上的床頭櫃,還擺著我們一家三口的合照。
那一刻,他徹底瘋了。
他把菜摔在兩人身上,把滿屋子的相片全都砸了個粉碎。
我媽就這麼看著他,把那個男人護在身後。
“沈浩,你鬧夠了就把門關上。”
“小宇回家看到了不好。”
她還記得我要回家,可和那個男人纏綿的時候,連門都不關。
後來的事情他們沒告訴我。
我隻知道,我爸要跟她離婚,問我願不願意跟他走。
我當然願意。
畢竟我親眼目睹了我媽出軌,我做不到跟她共處一室。
甚至為了替我爸出氣,我帶著幾個同學去了那個男人的家。
我罵他不要臉,把他家砸的稀巴爛,警告他別再出現在我爸麵前。
可我媽,很快就做出了反擊。
她沒有動我,她隻是替那個男人報了警,順便找了最好的律師。
“雖然你是我兒子,但子不教父之過,你敢欺負周然叔叔,你爸就得替你道歉。”
“這次隻是個小小的警告,再有下次,就算你是我兒子,我也不會放過你。”
我永遠記得那天,我被單獨留在警局。
我爸急匆匆地趕過來,當著警察的麵,給那個男人下跪。
他彎著腰,兩隻手的掌心都摳破了,跪在我媽和那個男人麵前,說:
“對不起,是我沒教好兒子。”
“他年紀還小,還要上大學,不能留案底,你們放過他吧。”
“我以後......以後一定會好好教他,不讓他再胡鬧了。”
“求求你們。”
那是我第一次,第一次恨不得我媽去死。
可我的恨沒有實現。
我媽還是活得好好的,甚至在那次之後,她連掩飾都懶得掩飾了。
她開始頻繁的帶那個男人回家,當著我的麵讓我喊他小爸。
她不在乎我爸整夜整夜的流眼淚,不在乎我每天看她的眼神都帶著恨。
她隻是全身心的,投入到了她的婚外情。
直到一個月後,我爸因為心神恍惚,出了車禍。
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媽哭。
4
我還記得,那是醫院最後一間單人病房。
我爸因為麻藥睡著了。
我媽握著他一隻手,眼眶紅紅的。
“老公,我們別鬧了好不好?”
“以後我們好好過日子。”
我爸大概聽見了,眼角劃過一滴淚。
沒說話。
那天之後,我媽就像變了個人。
她不再提那個男人,也不再徹夜不歸。
每天八點準時來醫院陪我爸做檢查,下午推著我爸去花園閑逛。
好像又變回了從前那個好妻子、好母親。
我爸還是不跟她說話,卻也沒再趕她。
甚至有一天晚上,他悄悄問我:
“小宇,你想要一個完整家的嗎?”
我知道,他還是舍不下的。
要是以前,我肯定會立刻拒絕,擺出一大段例子告訴他別相信女人會回頭。
可是,我爸車禍很嚴重,差點就死了。
看著他消瘦的身體,我沒辦法再刺激他。
於是我說:
“聽你的。”
事情似乎慢慢好起來了。
直到那天醫生讓我帶我爸去三樓做CT。
那個男人扶著我媽,從婦產科走出來。
我爸再一次崩潰了。
他嘶吼著,質問我媽不是要好好過日子嗎?
為什麼懷孕了?還要不要臉!
我媽臉上的笑僵住,她忽然就上前給了我爸一巴掌,恨恨地說:
“我不要臉?你十八歲就進廠打工,連本科學曆都沒有,你有什麼臉?”
我血液騰地一下衝到了頭頂,像隻瘋狂的小獸,想咬死這些欺負我爸的壞人。
可我還太弱了。
打不過一個四十多歲的成年男性。
我被扇掉了兩顆牙,鼻子血流不止。
我爸急壞了,明明還坐著輪椅卻拚命想要保護我。
最後,賀晴和那個男人贏了。
她牽著那個男人的手,丟下一句:
“離婚!”
揚長而去。
我腫著一張臉,看著我爸被護士送入手術室。
他的傷口崩裂了,大出血,止都止不住。
......
再後來,離婚協議寄到了醫院。
爺爺從鄉下趕過來,陪我處理爸爸的後事。
我仿著爸爸的筆跡,在離婚協議上簽下他的名字。
到現在,剛好八年。
客房的門被人敲響,老婆叫我和二叔去樓下吃晚飯。
我正忙著找紙巾擦眼淚,手機鈴聲忽然急促地響起。
竟然是酒店前台的號碼。
我以為是婚禮場地又出了問題,趕緊接了起來。
可電話那頭,傳來的竟然是賀晴顫抖的聲音。
“小宇,酒店的人為什麼說......你爸沒了......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