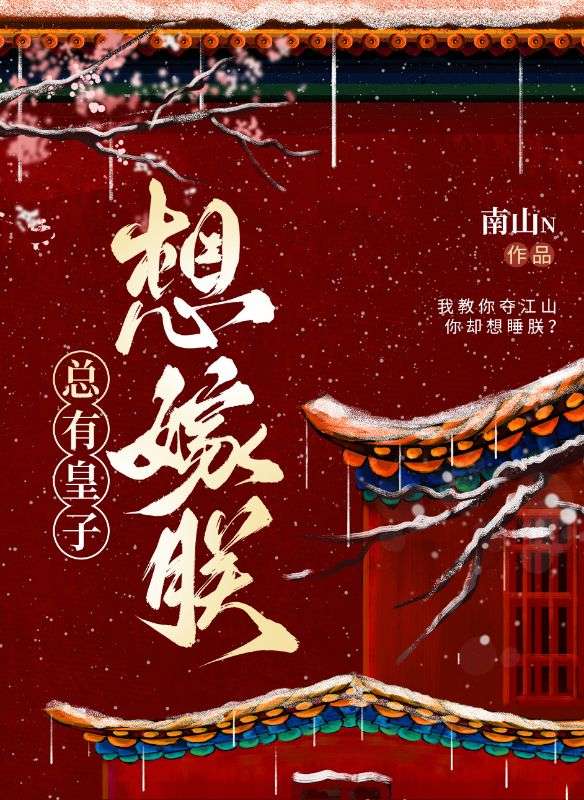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
第15章
訛錢
“將不棄,給你臉了?又給我派活兒?”
李承昊快步走。
將離舔著臉跟著他,“你瞧瞧,它沒了娘多慘啊。我又不會養,萬一養死了怎麼辦?你就當幫幫我?”
“求求了。”將離朝他撲閃著眼。
李承昊被鴉羽長睫刷得心都酥了,嘴上還在較勁,“看你求我的份上,勉為其難吧。”
將離打了個哈欠,“我乏了,送我回去。”
折騰了一夜,幸好今日休沐,不需要上朝。
她自顧自抱著黑豹蹲了下來,李承昊隻好去解開韁繩,牽馬過來。
“讓你得意的,還要爺我伺候你。”
“你帶我出來的,不得將我送回去?”
“不回了。將你殺了埋這裏,再種一片花海,明年春天來,花香遍野。”李承昊翻身上馬,又朝她伸出手,拉了她上馬,埋頭一嗅,“你用的什麼香?就種這個花。”
“天然自帶,總督羨慕不來的。”
將離摟緊小黑,笑意忍不住又溢出了眼眶。
“避暑,去嗎?”李承昊想了想,“湯憲督辦有功,應該會在避暑名單上。爺送他上青天。”
“我盡量吧。如果顏直不去,我應該能去。”
“老匹夫避什麼暑,我去打殘他的腿,讓他出不了雀都。”
將離被他逗得大笑,“行,打得時候注意,他家有悍虎。”
“悍虎有何懼,讓小黑去咬她。”
“小黑又不是狗。”
“那你去咬她。”
“嘿!李承昊!”
“輕點,敢打爺爺,我把你扔下馬!”
朝陽浴火,萬物複蘇、生生不息。
李承昊自入雀都後,第一次心情燦若朝陽:“哎,你還有妹妹嗎?”
將離愣了愣,垂下眸低笑:“有啊。”
“真的?”李承昊來勁了,“在哪?”
“將之瑤,你不是見過。”
李承昊大失所望,“切。”
琉羽一見到將離平安歸來,差點哭出聲。
她沒通行令牌,又不知道李承昊將她帶去了哪,隻能在府門口蹲一夜。
“你可回來了!再不回來我就要去找師父搬救兵了。我讓將不棄派人找你,他說大晚上出城不方便!說的是人話嗎!額……這狗哪來的?”
“這是豹子,李總督的。”將離掏出絹帕給她擦眼淚鼻涕,順手將黑豹側身放了放,“別想燉它。”
琉羽收回了哈喇子,瞥了瞥李承昊,嘟嘴:“總督該不會養大燉肉吃吧?”
李承昊手指來回搓著眉心,故作凶狠:
“小丫頭,總督我喜歡吃人。特別是圓頭圓腦的,最是肥美。”
琉羽嚇到往將離身後躲,將離一笑,摸了摸懷裏的小黑,把豹子遞給他:
“回去吧,我也進去了。”
李承昊接過豹子,深深看了她一眼,終於忍不住抬手將她璞頭帽上的雜草取了下來。
“那我……走了。”
“嗯。”
將離噙著笑,眉眼在晨光中璀璨如琉璃。
李承昊帥氣利落地翻身上馬,揚鞭飛馳。
琉羽看了看將離,“師姐,我總覺得哪不對……”
“哪不對?對的很,走吧。”
將離刮了刮她的鼻子。
琉羽剛跨出去一步,又拍了拍腦袋,“不對!馬是咱們的!”
將離愣了愣,可回頭看,哪還有李承昊的影子。
“下回去李府牽回來就是。”
總要再見的,她笑了笑。
兩人回到翠竹軒,將不棄已經等著了。
一見到他,將離的笑容冷了下來。
“回來了也不說一聲。”將不棄很不高興,“又同李承昊打架了?”
將離低頭看了看,月白色外袍沾滿了泥巴,胸口還有斑斑點點小黑的爪印,是挺狼狽的。
怪不得琉羽哭得那麼慘,挺像是被活埋了挖出來的。
“不挨頓打他怎麼消氣,為你挨的,賠錢吧。”
將不棄又無語又心虛:“市儈小人,又想訛我多少銀子?”
“差點被他活埋,我要你三千兩不多吧?”將離扯起破爛的衣角,“光這身衣裳,金縷閣收了我三百兩,還不算這玉佩,你看,都裂了。再看看我的手,沒一寸好皮膚,要換成你,早被他打死了。”
“將離!你獅子大開口啊!”將不棄不情不願,有點多,他心疼。
昨夜可剛剛給了五千兩,將家再富,也不能這麼流油,跟泄洪似的。
“給你兩千。怎樣,同他和解了沒有?”
將離鼻孔哼氣:“他說二皇子又送錢又送女人,給的多。你有這力氣在我這討價還價,不如想想怎麼砸錢給他吧。”
“二皇子下手這麼快?”將不棄若有所思,“太子也不能落後。打聽他有什麼喜好了嗎?”
“他對浮雲山腳下那空地有興趣,說想要過去殺人埋屍,昨日找謝世忠要呢,你有心攀附,不如投其所好。”將離浮唇,“這消息當我免費送你,不收錢。”
那塊地雖然偏,但土質奇特,是她想要。
慧修不懂詩書但對格物地理、機關奇巧尤為擅長,將離小時跟著她閑走四方時曾聽她提過,這種紅鏽土之下藏有鐵礦。
管它有沒有用,先占了再說。
“殺人埋屍?”將不棄懷疑自己聽錯了。
“拜你所賜啊。”將離嗤笑,眸光冰冷,“殺我,埋我。”
將不棄摸了摸鼻子,知道她這是找茬呢。
“地雖歸皇城司管,但太子一句話,謝世忠不敢不答應。對了,昨日孟賀嶂遞了折子,說是尋著爹頭顱的下落,不日親自送回雀都。陛下心裏歡喜下了調令,擢升他回京入禮部任員外郎。爹的門生舊故,又對咱家有恩,可得好好籌備為他接風洗塵。”
將離斂了斂眸,昨夜她赴宴,謝世忠半個字都沒提,將不棄怎麼就得到宮裏的消息了。
他的耳朵倒是挺靈的,宮裏有人?
“侍郎人在家中坐,一點不耽誤運籌帷幄。”
“身為帝師,自然要眼觀六路、耳聽八方,方能走一步看十步,未雨綢繆。你這輩子也學不會,眼中隻有阿堵物,枉讀聖賢書。”
將不棄嫌惡,揚手讓雙慶推他走。
將離冷笑三聲,臭東西蹬鼻子上臉了。
“是,你清高,你不食人間煙火。兩千兩快點送來。”
琉羽偷偷豎起大拇指,高。
師姐訛錢有一套。
李承昊翻身下馬,長腿筆直,動作瀟灑。
海東青在空中盤旋,俯衝而下,落在了李承昊的肩上,低咕了聲。
“爺,無咎公子來了。”玄暉迎上來接過馬韁繩,眼睛直往他懷裏看:“喲,還真是個豹子啊?”
海東青鼻嗤了聲,桀驁地撇過頭。
李承昊將懷中豹子一並交給玄暉,再伸手摸了摸海東青光澤柔亮的羽毛,神情傲嬌中藏著幾分刻意:
“將侍郎救下的,叫什麼小黑。哼,求我給他養,我勉為其難答應了。去,給它喂點肉。”
“好嘞。”玄暉手一摻將豹子夾在腋下,牽著馬往馬廄走,又折回頭,“哎,不對啊。這不是咱府上的馬。”
李承昊這才想起來,黑眸一亮,“你把豹子先關進籠子。回頭把馬給將侍郎送回去,再取兩罐北冥特製的金瘡藥送他,就說是謝禮。”
“是。”玄暉納悶,不是將侍郎求您麼,怎麼您上趕著送謝禮呢。
崔無咎本是斜倚著紅漆大門,一襲寶藍箭袖,眉目靈動活潑,兩隻圓溜溜的眼睛早早就盯住了玄豹,跳下丹墀三步並兩步湊了過來,玄豹警戒地呲牙,試圖阻止他靠近。
“喲,哪撿來的?給我吧。”
李承昊伸手推開他的腦袋:“想得美。”
崔無咎摸了摸額頭,不滿地嘟囔:“我還是個孩子啊!給我又能怎麼了。”
“二十還叫孩子?人衛淩豐二十屁股後頭都掛仨孩子了。大理寺這麼閑,不用查案了?大清早蹲我這作甚?”
李承昊白了他一眼,背著手朝府內走,嘴裏還哼著小調。
“你還不是二十了,照舊打光棍,還說我。”崔無咎勾肩搭背:“心情不錯啊,昨夜在哪風流呢?”
他是國子監祭酒崔永真的孫子,崔家三代單傳的獨苗,李承昊光屁股時就認識的玩伴,可詩文不行、武藝不精,隻喜歡查案,非要去大理寺做個小小寺丞,日日樂此不彼。
崔老大人疼孫子,小勸過幾回也就隨他去了。
“有時間在我這閑晃,不如花點腦子查一查湧安的死,你別和我說,你們大理寺就這點本事吧?”李承昊想起這事就惱火。
湧安陷害北冥死不足惜,但隨便拉出個替死鬼就想把這件事翻篇,大理寺這幫豬,一點骨氣都沒有。
崔無咎更氣:“嘿!為這事兒剛同周開原打了一架,要不然怎麼來找你呢!衛家推出來的凶手在牢裏自盡了!這還不算,人還在牆上留血書,說是你指使的!”
李承昊一口老血差點噴出來。
幹他老子的!
又關我事?!
李承昊打上大理寺,狠狠鬧了一通。
大理寺周開原前腳剛被崔無咎打腫了左臉,後腳又被李承昊打了右臉,眼睛像熊貓,腦袋腫得像個饅頭,包著大白布在禦前哭哭唧唧。
“陛下,臣還沒說什麼,李總督不分青紅皂白,就對臣動手。”
皇帝一個眼神,總管太監潘德海湊過去查看傷勢,“喲,這都破相了呢。”
“李承昊,你真是無法無天,北冥王素日就是這麼教你的?”
太後撥開珠簾走出來,滿臉慍怒。
周開原娶了蕭家旁支的姑娘,算起來也是太後的姻親。
“大理寺聽察情、掌刑獄、雪塵冤,可我看周大人的眼睛不太行,我這是給他洗洗眼,怎麼無法無天了。再者說,李長白一年四季忙著打仗可沒空教我,同他又有什麼幹係!”
李承昊是半點麵子都沒給蕭太後。
左右都困在這雀都,他偏就橫了,看誰敢拿他怎樣?
皇帝手扶著額,斜斜地靠在龍椅上,滿眼都是疲倦:“咳咳……好了。長煦是衝動了些,但周開原也不是沒有錯。這件事明顯就是栽贓,你一個大理寺卿難道還看不明白?凶手死便死了,這點小事鬧上朝堂,也不嫌晦氣。”
啊?周開原勉力睜大青腫的眼,可依舊隻能露出一條細縫,他冤呐!
他什麼都沒說還挨了頓打,怎麼還是他的錯了?
“陛下……臣……”他委屈啊!
太後端著臉瞥了他一眼,微微搖頭。
他低下了頭,自認倒黴:“陛下教訓的是,臣知罪。”
“長煦啊,雀都比北冥可熱多了。過幾日陪朕去芙蓉山莊避暑,消消火氣。無咎也去,你們正好做個伴。都下去吧,朕也疲了。”
二皇子跪在一旁,眼珠子轉來轉去,“父皇,那兒臣呢?”
“你若想去就一起去,老實點,別盡給朕添堵,去看看你母妃,她想你了。”
“謝父皇!”二皇子歡天喜地地告退。
太子垂首立在一旁,像被遺忘的人,有些茫然無措。
“哀家歲數大了,天熱懶得動,這回就不去了。”太後意興闌珊,搭著老嬤嬤的手,也不等陛下回話,就先一步走出大殿。
皇帝望著她離開的背影,劇烈地咳嗽了幾聲,再抬眼,目光又痛又恨,語氣卻依舊平靜:“送母後。”
李承昊帶著崔無咎告辭。
等人都走光了,潘德海才扶起皇帝,“陛下,今兒您沒吃藥,也能坐小半個時辰了。奴才瞧著這回靈丹頗有奇效啊。”
“咳咳,但願吧!”皇帝想起幾個皇子,邊走邊搖頭,“這幾個小子少惹我生氣,朕還能多活幾日。”
“陛下洪福齊天,如今李世子也回到您身邊,遂了多年心願,老奴瞧著心裏真歡喜。”潘德海抬袖擦了擦眼角。
“你瞧瞧,他的五官同他娘一模一樣,但眉眼像朕。想起雲茵,朕的心裏難受啊。當年她棄我而去,誰能知道肚子裏已經有朕的骨肉。若不是母後強壓著我娶謝氏,我又怎會對不起她。”
潘德海垂頭勸道:“也是她沒福氣,皇後雖說不能落她頭上,可做您的寵妃照樣榮寵一世,也不必在北冥吃糠咽菜受罪,若是在宮裏頭生,哪能難產而死啊。”
“哼,李長白還以為能瞞得了朕一輩子,朕不會就這麼算了。”皇帝手捏得發緊,骨瘦如柴的手背青筋陡起,如一條條蜿蜒的蚯蚓。
潘德海低垂著頭,試探道:“陛下,世子體健貌端,又擅騎射,假以時日未必不能……”
“哼!”皇帝斜睨了他一眼,“是有人讓你來打聽朕的心意吧。”
潘德海立即跪了下來掌嘴:“絕無此事!奴才多嘴!”
皇帝讓他起來,冷哼了聲,繼續搭著他的手往養心殿走:
“讓他回雀都,朕的確有私心。一來想著全一全父子情誼;二來,也正好用他磨一磨儲君的刀子。老大過仁、老二過奸,雖說儲君已立,但朕心裏總覺得差了些什麼。這兩人要是聰明的,就該好好對他。
若說聰慧謀略,他是朕的兒子,自是人中翹楚。可他上來,雀都的世家就不得安寧了。這些年他們鬥得你死我活,朕瞧著解氣。沒得讓他們有借口扭成一股繩,反倒生出禍事。”
“陛下英明!”潘德海諂媚地迎合著。
皇帝的心情也逐漸轉好:“讓內庫挑些珠寶玉器和有趣的玩意兒送去總督府上。他進雀都還沒幾日呢,有些人就耐不住想拿他開刀,受了不少委屈。”
“陛下拳拳愛子之心,總督就算是石頭心,也定然能感化的。”
皇帝長歎息:“他的脾氣同他娘一樣,倔。”
縱然他同他講了不少當年之事,李承昊死都不肯認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