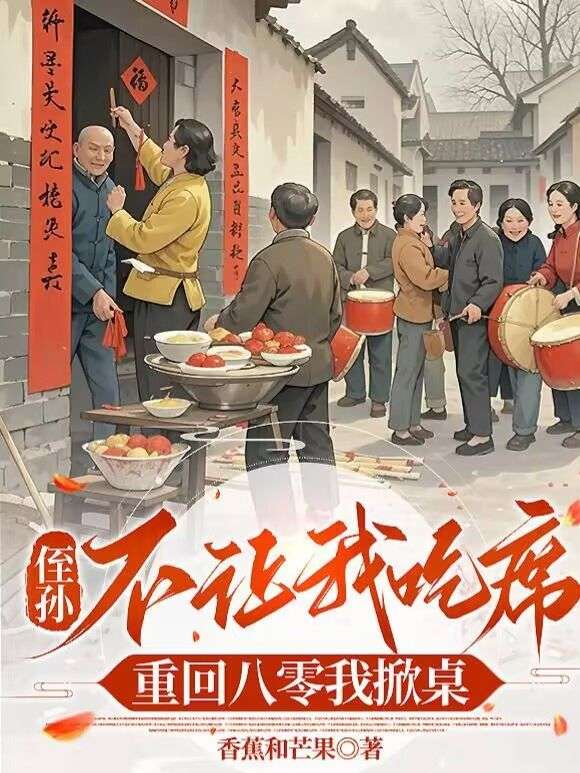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
第9章 一百塊買斷的狗屁親情
莫莉莉渾身一抖,猛地撲上去,一把扯斷了蔣蘭腰間的褲帶繩,從裏麵拽出一個縫得嚴嚴實實的藍布包。
“我的錢啊!作孽啊!”蔣蘭一屁股坐在地上,雙手拍著大腿,哭號聲震得房頂灰直掉,“養了你這麼個白眼狼,聯合外人來搶親媽的錢啊!我不活了!”
莫莉莉根本聽不見。她手忙腳亂地撕開布包,裏麵的票子撒了一地。
大團結,五塊的,兩塊的,還有一堆毛票。
這是莫家吸血吸了多少年攢下的家底。
莫莉莉跪在地上,一張一張地撿,手抖得像篩糠。她顧不上數,抓起一把就往桌上拍。
“給你!拿著滾!拿著滾啊!”
賀長征沒動。
他看著那一堆皺皺巴巴的錢,心裏卻在算另一筆賬。
“三十是賣糧食的錢。”他開口,語速很慢,每一個字都咬得極重,“結婚五年,雲嵐每個月工資二十八塊五,每個月往娘家拿十五塊。一共九百塊。”
莫母的哭聲戛然而止。莫莉莉撿錢的手僵在半空。
“我不貪心。”賀長征從兜裏掏出一張皺皺巴巴的紙,上麵密密麻麻記著賬,“那些算是孝敬。但這幾年,你們以前借著給小弟看病、給家裏修房,從我手裏單獨借走的,一共七十塊。”
他把那張紙拍在桌上,連同那把扳手一起。
“加上賣糧食的三十,一共一百。”
賀長征抬起頭,盯著莫母那張慘白的臉。
“少一分,我就去廠裏找你們領導聊聊。”
堂屋裏死一般寂靜。隻有座鐘還在不知死活地走著。
一百塊。
在這個豬肉七毛八一斤的年代,這是一筆巨款。
莫母從地上彈起來,指著賀長征的鼻子就要罵,可手剛伸出去,就看見了那把黑沉沉的扳手,又硬生生縮了回來。
“給......給他!”莫莉莉絕望地喊了一嗓子,她把地上的錢全都攏在一起,甚至把蔣蘭口袋裏剩下的幾張零錢也掏了出來,一股腦推到賀長征麵前,“都在這兒了!一共就一百零幾塊!都給你!你快滾!這輩子別讓我再看見你!”
賀長征伸出手。
那隻常年握著鉗子扳手、滿是老繭的大手,此刻在劇烈地顫抖。
不是因為怕。
是因為這遲來的公道。
這一百塊錢,每一張都浸透了雲嵐的委屈,每一張都刻著他們小家的血淚。
他一張一張地數。
一、二、三......
莫家母女死死盯著他的手,像是看著他在割她們的肉。
九十八、九十九、一百。
賀長征數出一百塊,揣進貼身的襯衣口袋裏,那是離心口最近的地方。
剩下幾張零錢,孤零零地躺在桌上。
他站起身,提起扳手,插回後腰。
“兩清了。”
說完,他轉身就走。
那一刻,壓在他脊梁骨上五年的大山,好像突然挪開了。
身後傳來莫母惡毒的咒罵聲,像是積攢了一輩子的怨氣終於找到了出口。
“賀長征!你個喪良心的東西!你拿了這錢也不怕爛手!你逼死娘家人,你不得好死!出門就被車撞死!讓你斷子絕孫!”
罵聲尖利,穿透了院牆,引得胡同裏的鄰居紛紛探頭探腦。
賀長征腳步一頓。
他站在院子門口,背對著那個曾經讓他唯唯諾諾、連大氣都不敢出的家。
夕陽西下,將他的影子拉得很長,顯得有些蕭瑟,卻又無比挺拔。
他慢慢回過頭。
莫母正站在堂屋門口,叉著腰,唾沫星子亂飛,那張臉因為憤怒和心疼而扭曲變形。
賀長征看著她,就像看著一個陌生人。
“媽。”
這是他最後一次這麼叫她。
“我再不得好死,”賀長征拍了拍胸口那疊滾燙的鈔票,一字一頓,“也不能看著我兒子餓死。”
說完,他拉開那扇吱呀作響的破木門,大步走了出去,頭也沒回。
隻留下身後莫母被噎住的抽氣聲,和那扇在風中晃蕩的木門。
門外,殘陽如血。
賀長征朝家走去。
風刮在臉上,生疼,卻痛快。
他摸了摸胸口鼓囊囊的錢。
兒子可以上學了。
雲嵐也不用半夜躲在被窩裏哭了。
至於莫家?
去他媽的體麵。
他猛地一拐車把,車輪碾過一塊碎磚頭,顛了一下,卻穩穩當當地衝進了前方的暮色裏。
路邊的電線杆子上,一隻麻雀受了驚,撲棱著翅膀衝上天空。
回到家時,天已經擦黑了。
屋裏沒點燈。
賀長征推開門,借著月光,看到賀雲嵐坐在床邊,身子繃得筆直。
聽到門響,她猛地站起來,動作太急,帶翻了腳邊的小馬紮。
“長征?”
聲音發顫。
賀長征反手關上門,拉亮了燈繩。
昏黃的燈光瞬間灑滿小屋。
他走到桌邊,從懷裏掏出那遝錢,“啪”地一聲拍在桌上。
“數數。”
賀雲嵐看著那堆錢,眼淚唰地一下就下來了。
她沒去數錢,而是一把抱住了賀長征的腰,把臉埋在他那件沾滿機油味的工裝上,放聲大哭。
哭聲裏全是委屈,全是愧疚,也全是解脫。
這麼多年,她夾在娘家和丈夫中間,裏外不是人。她想幫襯娘家,卻換來變本加厲的索取;她想顧好小家,卻總是力不從心。
今天,這把刀,終於由賀長征替她斬斷了。
“行了,別讓人聽見。”賀長征的大手在她背上笨拙地拍了兩下,“文文呢?”
“在裏屋複習呢。”賀雲嵐抹了一把臉,吸了吸鼻子,這才把目光落在桌上的錢上。
她顫抖著手,開始一張一張地數。
“十,二十,三十......”
賀長征拉開椅子坐下,點了根煙。
煙霧繚繞中,他看著妻子的側臉。
這幾年,她老得快,鬢角都有白頭發了。
“一百塊。”賀雲嵐抬起頭,眼睛紅通通的,“多了......比咱記的賬多了。”
“那是利息。”賀長征彈了彈煙灰,“給文文留出學費和生活費,剩下的,你去扯幾尺布,給全家做身新衣裳。再買二斤肉,明晚包餃子。”
“哎!哎!”賀雲嵐連聲應著,眼淚又止不住地往下掉,但這回是高興的。
裏屋的簾子掀開了。
賀文走了出來。
十六歲的少年,個子竄得快,已經快趕上賀長征高了,就是太瘦,像根竹竿。身上那件確良襯衫洗得發白,袖口短了一截。
他看著桌上的錢,又看看紅著眼的母親和抽煙的父親。
“爸,媽。”
賀文走到桌邊,低著頭。